“既然幸存,就要乐观”。快乐,大概是伊凡·克里玛给人们留下的最深的印象。上个月,他以94岁的高寿逝世,在他漫长的作家生涯中,他所属的国家在久经战乱后,又长久处在晦暗之中,他自己和许多普通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一样,住平庸的陋屋,干过类似扫大街那样的简单工作。但在克里玛的文字里,乐观的气质向来不会缺少。

他生于1931年,因为是犹太人,二战期间他全家都进过集中营。据官方统计,从1938年到二战结束,捷克斯洛伐克共有26万犹太人死于迫害和屠杀。在捷克,最有名的集中营当数特雷岑,少年克里玛就曾被关在那里。不过,他总是本着一种“我已幸存”的心态回忆那时的事的,为此,语句中不仅少了阴郁,反而有少年的新奇:
“在一个阴沉的秋日——可能是1943年的一个清晨,因为父亲还和我们在一起——他们把所有人赶出城镇,赶到一片巨大的草地上。”
日期是不确定的,显示了少年记忆的模糊,在模糊的描述中,部分场景清晰了起来。克里玛记得女人的哭嚎:
“这些女人哀叫说:我们这是我们活着的最后一天了,他们会开枪打死我们,要不就向我们中间扔炸弹。仿佛是为了证实她们的恐惧,一架飞机从头顶掠过,机翼上有一个黑色十字架。”
在特雷岑,纳粹没有遽然发动屠杀,而是做一种“正常化”处理。让犹太人正常生活,以此对付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的干预。克里玛写了他当时的体会:虚假的“优待”并没有换来他冷冷的事后嘲弄,相反,他不无好奇地回想起当年他们全家人拿到的纸币:钞票的正面刻着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,怀里抱着一块石碑。母亲指着石碑说,这是摩西和他手捧的律法法版,法版上刻着十诫,人们应该依据这些诫命行事。对于犹太教,克里玛是不熟悉的,他全家也基本被欧洲同化,家庭生活中并没有多少犹太仪式的印记。但克里玛记下的这一插曲暗示,他是在集中营里,第一次了解了自己真正的“民族属性”——实际上,这种“被恶意针对后才得知自己(在他人眼里)是谁”的经验,绝不仅限于犹太人。
克里玛全家都活了下来,完好无损,这很神奇。他把活下来这件事比喻为“在一场可恶的抽彩游戏中抽到了为数不多的幸运数字之一”。在大屠杀、集中营题材的文学、艺术作品中,不论是驰名全球的电影《辛德勒名单》《苏菲的抉择》,还是普利莫·莱维的《这是不是个人》和埃利·威塞尔的《夜》,总少不了一种或阴郁或忧愤的调性,可是在克里玛这里,幸运的感觉,始终决定了他叙事中的选材和语气。他把自家的幸运,看作这个世界“奇怪”“疯狂”的一个证明:世界安排几十万人死去了,又安排另一些人,一些和那些死人明明属于同族同胞的人,活下来,进而还安排像他——伊凡·克里玛这样的人,用时不时乐淘淘的笔调去讲述这个世界。
克里玛的母亲有两个兄弟是共产党员,都被德国人所杀。因为家族中出了烈士,1948年后,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,克里玛的家庭得到了不错的待遇。新政权给像克里玛这样,在战前缺乏系统教育的年轻人灌输正确的思想,当他一面想当作家,一面想找一些“超纲”的作品来读的时候,他发现困难重重。
克里玛认同国家采取的道路,同时也尊敬他身为电机工程专家的父亲,但父亲因为一个那年头常见的罪名——破坏经济计划罪被逮捕下狱时,克里玛稳固的信念遭到重创。父亲被判监禁20年,不幸中的万幸再次降临他家:1953年斯大林去世,父亲也得以脱罪。那时,克里玛便开始构思小说。如此年轻的作家,若要一时有成,必须用透他手头有限的人生阅历,或者,必须把以“我”为主的表达较为老练地写出来,让读者对“我”产生持久的兴趣。克里玛写过一篇短文叫《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》,他毫不做作地说,我是个幸运的人,我的快乐性情源于我的确没有经历过多少实质性的痛苦:
“那时,有些比我年长的人经历了一些事……他们相信,这些事随时会卷土重来。但我不一样……我觉得,我经历的事再也不可能重复,因为我幸存了下来。我总是满怀一种期望:就算我再度遭遇那些事,我也会幸运地免于其一切伤害。”
27岁结婚,并且早早有了两个孩子,克里玛在1960年代初,一面搜罗自己能找到的书,全力去理解苏联和东欧在这十几年里发生了什么,一面写一些故事和戏剧。他加入了作协,和其他文学创意人一样,他要靠“曲笔”,靠隐喻性的写作,来避开审查,同时尽力做到诚实,纵然不能揭示社会的真实样子,起码不能对眼前之事和切身的感受故作无知。他不无骄傲地宣称畅销是一本书劣质的证明,因为书中必然充满了陈旧的短语和老套的情节,以迎合大众的口味。
60年代的克里玛一如那时年轻人的时尚,开始留披头士发型,厚厚的、野性的两鬓盖住了耳朵。那正是捷克新浪潮电影蓬勃的时期,1914年出生的捷克小说家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此时分外活跃,他的短篇集《底层的珍珠》以及中篇小说《严密监视的列车》都在1966年被改编成电影上映(导演都是门策尔),后者还于1968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;米兰·昆德拉的《玩笑》出版后颇为轰动,很快也得到了电影改编,上映于1969年,是“新浪潮”期间最后上映的一部作品。
虽然克里玛那时写的几部作品都没得到电影改编的机会,但他也挺幸运地得到出国的许可,去过英国,访问过以色列的基布兹,还到美国德克萨斯讲学。1968年“布拉格之春”前的风雨动荡之中,昆德拉积极参加抗议活动,为新浪潮电影人辩护,而久在党内的克里玛则援引马克思的相关论述,来声扬创作人的创作自由。
克里玛比昆德拉小两岁,“布拉格之春”前后,青春正盛的他(如其在回忆录《我的疯狂世纪》中所说)除了参与公共活动外,还搞了两次外遇,随后,在得知签证即将被中止时,他要做出抉择: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都移民出去了,包括他的一些好友。他该何去何从,是回归布拉格、回归家庭,还是留在西方?
他回来了,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。在一张1973年拍摄的照片里,他和昆德拉二人留同样的发式,看上去正在为什么事一起嗤嗤发笑,笑容极具捷克人的特点,有种狡猾而放荡的味道。昆德拉是1975年最终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的,他定居法国后,逐渐为西方读者所知,1984年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更是被西方读者看作一扇窥视东欧社会的窗口。昆德拉显得超脱,世外高人一般,执定“人类一思考,上帝就发笑”的理念,在《生命之轻》《告别圆舞曲》《慢》等作品中,他把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纳入一种整体性的荒谬图景之中,以某种宏观的历史规律吸纳局部的不公,弱化个体抗争强权的道义感召力,几乎把压迫看作对被压迫者的一种“成全”,用来证明世界之荒谬的真相。
西方读者在接受了昆德拉讲述的事实的同时,也把昆德拉对此的态度,还有他的写作风格一并接受过去,视为“捷克范儿”:黑色幽默,荒谬,加上对性爱的赤裸裸、火辣辣的痴迷。克里玛没有移民。他的作品在1970年代已被禁,境遇的反差或许会使人感到他和昆德拉必然分道扬镳,日后,克里玛的作品逐渐翻译成英文和其他语言时,二人的区别也能从译文里一眼看出:昆德拉高冷,“哲理向”鲜明,写的故事是给那些希望体会深刻的人看的;而克里玛“就事论事”的时候更多,语言直白不拐弯,好以第一人称写亲眼目睹、亲身体会的事情。
但两人的共同点也是明显的。用最浅显的话讲,他们对于性爱、情人等主题有同等的痴迷。对此的解读可以是这样的:在高度压抑性的社会氛围中,情爱的时刻,一方面是个体品尝稀有的自由的不二之途,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发泄,人们用纵欲耗尽自我,缓和对那个巨大阴影的恐惧。
在1970年代,美国作家菲利普·罗思多次到布拉格,与克里玛交上了朋友。两人的对话很多,形成文字后有很高的质量。罗思说,克里玛是教他去看“真实生活”的人:70年代初,被作协“下放”出去的作家,做着像清洁工、搬砖工、兜售雪茄烟之类的工作,以此谋生;克里玛也不例外,他扫过大街,还在医院里担任过秩序维护人(他说,因为医院免费医疗,秩序难免混乱)。他引着罗思看到这些,虽说“真实”未必一定意味着沦落、不体面、苟延残喘,克里玛本人也未必能展示全部“真实”,但一个诚实的作家一定会承认,世界的真实的一面,人类生活的真实的一面,一定是偏向于琐屑、偏向于缺乏光彩的。
克里玛似乎在70年代末之后渐渐得到了出版机会。1986年,他拿出了《爱情和垃圾》(英译本1990年问世),罗思称这本书是“反向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”,然后他又写出长篇《我的金饭碗》。单看他出书的频率,你会误以为这是一位处在黄金年龄的多产作家,一定忙着到处巡回签售,发表演讲,上电台电视讲话;你断然想不到,时年已经50多岁的克里玛,那会儿竟还扫过大街,因为他的作家身份始终不被承认。《爱情与垃圾》就是他上街扫垃圾后写出来的,当时是“地下出版物”。“垃圾”构成了“爱情”所需的对立面。
1989年,他好不容易领到了退休金,终于退休了。早年的幸存是不是预支了他人生的运气额度,才使得他半辈子都无法像个职业作家那样活着?退休后不久,他的老友、也是文坛同行瓦茨拉夫·哈维尔选上了总统,邀请他也来政府里当一份差,他拒绝了。之后,克里玛的书才陆续进入市场,不断被翻译成各个语种,到21世纪,回忆录《我的疯狂世纪》把他的知名度推到顶峰。
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虽然早有声名,但他毕生创作的最高成就——中篇小说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,同样是在1989年才终获出版。克里玛似乎是择定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,后来几度窘迫也没有离开。他和赫拉巴尔也颇有些相似之处,他们的小说里颇多自传色彩,对于在捷克的真实生活,如劳动的琐碎、居住条件的简陋,如知识分子和普通体力劳动者的混淆,以及情爱方面的坦荡热切,都有很多描写。不过,无论是1968年还是1977年,赫拉巴尔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政治上的压制,克里玛就不一样了,他常年无法出版作品,他坦率直露的表达方式让他始终受到怀疑。
在《我的疯狂世纪》中,他这样解释1990年他拒绝哈维尔政府的任职邀请的缘由:“我曾短暂地相信,一个人如果不想浪费一生,他就有责任设法拯救世界。这段相信的时间已经过去,如今我想继续做一件我懂得如何做的事:写作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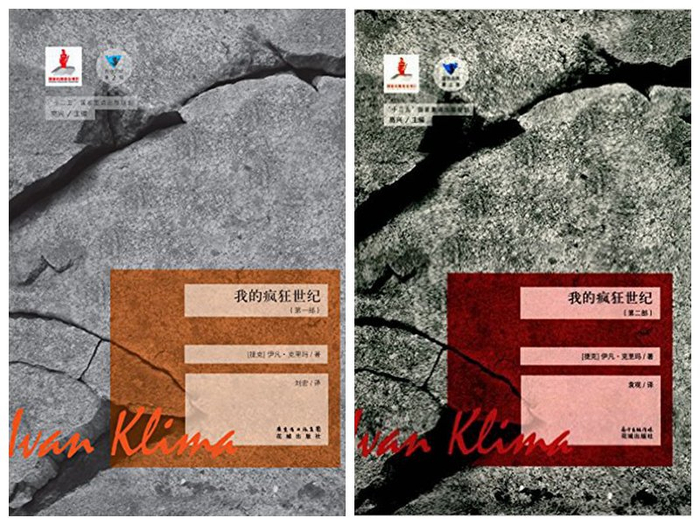
《我的疯狂世纪》第一部、第二部
[捷克]伊凡·克里玛 著
花城出版社
https://finance.sina.com.cn/jjxw/2025-11-24/doc-infynrph3985309.shtml


Leave Your Comment Here